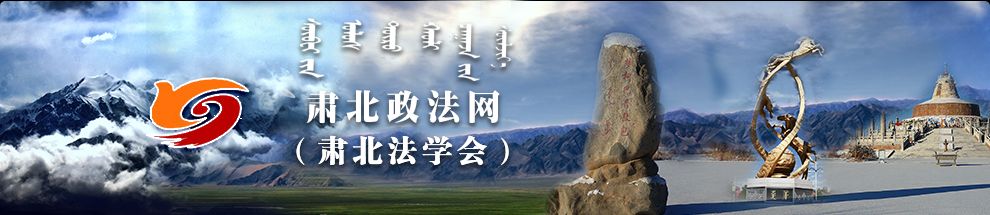因时而变 随事而制:云南法院司法改革掠影(上)
时间: 2016/10/28 10:51:29
因时而变 随事而制
——云南法院司法改革掠影(上)
背景介绍
云南省是全国第二批司法改革试点。在改革中,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始终坚持突出司法责任制,因时而变,随事而制,在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改意见基础上,制定出台《云南法院健全审判权运行机制完善司法责任制改革试点意见》、《云南试点法院审判权清单》等改革制度,为规范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提供了明确指引,办案团队组建及分工协作、案件繁简分流、双轨制办案等方面形成了良好的制度机制,为云南法院司改工作的全面推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不久前,云南省司法改革试点法院第三批法官入额考试如期举行,3752名法官参加了这次遴选笔试。8月份,云南全省16个州市48个司法改革试点法院结束了第二批法官入额遴选笔试考试,考核遴选工作紧锣密鼓稳步推进。目前,云南法院法官入额遴选笔试全面结束,司法改革全面推进工作将迈入新的阶段。
新选择,心选择
2014年9月,云南启动省内试点法院改革,昆明、普洱两个中院及昆明市西山区、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普洱市思茅区、景谷县等四个基层法院结合自身的民族、区域特色开展了多项探索。
面对各地法院案件受理量明显不均的现实状况,39%的员额配比如何分配成为司改中要解决的第一个难题。有的法院半年收案逾两万,而有的法院全年收案仅两千,案件数量如此悬殊,员额配比“一刀切”显然不符合实际。云南法院决定“两步走”:综合考虑全省各地办案数量、地区差异、人口比例、办案成本等因素,在39%的员额幅度内预留5%作为机动调配员额,试点期间执行34%的比例上限,首批遴选实际比例不超过25%。
“41名审判员首批只遴选出16名员额法官,我们力求做到‘不抛弃,不放弃’。”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院长吕垠松介绍,该院科学制定考核办法,统一入额条件和程序,将包括副院长在内的所有审判员、助理审判员纳入同一平台进行遴选,不搞论资排辈、迁就照顾。
景谷法院刑二庭法官叶德敏今年已经59岁,是云南法院首批入额法官中年龄最老的。“做了一辈子的法官,不能在这个时候‘掉链子’,我希望将来能够告诉孙女,‘爷爷是名法官’。” 而57岁的段玉祥却有着不一样的想法,“成为员额法官固然很好,但是现在的办案压力怕自己身体会吃不消。”他最终选择法院其他的工作岗位。54岁的彝族法官周坤怀揣速效救心丸走上考场,却在全省首批法官入额考试中勇拔头筹,成为景谷法院刑事审判团队中的入额法官。辛苦一辈子,周坤希望到退休时,能够突破基层职级待遇瓶颈,在法官等级待遇上有所提升。这也是许多竞争入额的法官心中的企盼。
昆明中院知识产权庭审判员王瑞在经过第一次初选考试后,未能如愿进入首批员额。在“双轨制”办案模式下,王瑞一面承担着一定数量的案件审理任务,一面积极备战接踵而至的下一轮考试。刚刚考上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博士研究生的张霞,因工作调动的缘故,无缘入额法官,被昆明中院任命为第一批法官助理,此前她是曲靖中院民一庭具有十多年办案经验的审判员。由“红花”变“绿叶”,张霞虽工作热情不减,但也期待能早日出台相应的配套措施,为法院人员的科学流动创造条件。
考什么,怎么考
如何通过考试、考核,把专业素质高、办案能力强的优秀法官遴选到办案一线岗位,不仅关系每一个法官的个体命运,更直接关系到司法改革的成败与实效。
云南司改启动首批试点考试时,只设置刑事、民事、行政三种类型的“案例分析”题型,突出对证据审查判断、案件事实认定、法律法规运用、法律文书写作等实务能力的考察。在今年8月3日开展第二批入额考试时,适时对试题进行“升级”改造,增设了商事案例和简述题。
为避免考试程序的虚置,云南高院合理划定了及格分数线,并对边疆民族地区适当放宽。从考试结果看,首批试点法院340名法官参加考试,及格率为73.9%,有的法院班子成员未达到及格线,考试淘汰、选拔的功能得到充分体现。
在随后的考核工作中,除了要求法官具有良好的政治素养、职业素养、较高的法律政策水平、与职业相适应的审判能力、3年至5年的审判工作经历等,司法办案经历、办案数量质量、所办案件有无过错瑕疵等工作实绩成为评判办案能力的重要因素,占到了考核总成绩的70%。
作为省会城市的昆明中院,在考核中更加注重打造职业化、专业化法官队伍,增加了对审判理论研究成果、信息化运用能力的考核。在考核分值上科学设置了5个方面28项具体指标,另外设置了5分的特殊业绩加分,让客观数据说话。考核既突出工作实绩,又突出资深法官的履职资历,也突出为法院作出的贡献,确保资深法官和年轻骨干法官的优势特长都能够在打分中得以体现。
整个遴选过程,法院领导干部入额问题受到普遍关注。云南法院试点员额制改革中彻底打破“行政化”观念,严控领导干部入额门槛。除院长外,所有参加初选的人员均按同一标准和程序进行考试、考核,其中副院长和具有法官职务的党组成员的考核由上一级法院组织实施。
“我们明确,不分管审判业务的院领导、党组成员首批暂不入额,为年轻骨干留出空间。”思茅区法院院长吴江涛介绍,这样可以有效防止“能办案的进不了员额、进入员额的办不了案”,让骨干法官有更多的职业尊荣感。
针对少数民族法官入额问题,云南试点法院也积极探索。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普洱市司法局政治部主任李松泉表示,云南民族众多,民风民俗各不相同,懂民族语言在工作中非常重要。他建议在政策上要对少数民族地区法官倾斜,扩大员额比例,提高待遇。
云南在司改方案中明确少数民族自治地方要有当地主体少数民族的法官入额,并可享受考试适当放宽等待遇。对试点法院少数民族候选人的考核,除考察办案经历外,还突出对掌握当地民族语言文字、了解民族习惯和民风民俗的情况及群众工作能力等方面考察。据统计,全省首批入额法官中,少数民族法官占比达20.9%。
“我们既要把最愿办案、最会办案、最适合办案的法官遴选出来,又要把最能反映法官工作业绩和能力水平的核心要素以定性、定量的形式呈现出来,让资深法官有归属、让青年法官有获得感。”云南高院副院长田成有如是说。
谁审理,谁负责
2015年3月,云南法院以人民法庭作为司法改革的“试验田”,在全省22个试点法庭建立了以主审法官为核心的“1+1+1”审判团队模式,对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进行先行先试,探索推进主审法官办案责任制。
作为试点的曲靖市麒麟区法院越州中心法庭,建立了由主审法官、法官助理和书记员组成的两个审判团队,由独任主审法官或合议庭对案件全权负责,直接定案,并制作、签发法律文书,主审法官、合议庭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对审理的案件质量终身负责。
随着改革深入推进,首批试点法院结合各自实际,组建了不同模式的审判团队。有的甚至打破庭室架构,实行扁平化管理,审判团队模式呈现多元化、专业化、特色化。
昆明市西山区法院取消了院庭长对案件的分案权、审批权,法官对承办的案件依法独立审理、裁判或参加合议庭评议,独立发表评议意见,独立签署法律文书。员额法官独立签发裁判文书占比大幅提升,达到结案数的99.8%。从今年6月16日起,景谷法院未入员额的庭长、副庭长的裁判文书改由员额法官来签发,真正做到了还权于法官、还权于合议庭。
改革释放出了新的审判生产力。2016年上半年,昆明市中院在受理案件数达23888件、审结各类案件16580件的情况下,一审案件上诉率比2015年同期下降了0.52%,服判息诉率上升0.52%;西山区法院审结案件5543件,同比上升64.53%,32名入额法官人均结案174件,做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思茅区法院结案率同比上升10.56%,案件审理周期从65天降为58天,同比减少7天;景谷法院一审服判息诉率达到97.36%,发改率仅为0.27%。
通过改革,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数量大幅减少,院、庭长开始走向审判一线,办案数量均比试点前明显增加。今年上半年,昆明中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87件,比2015年同期下降11.22%,院、庭长办理案件160件,同比上升171.19%;西山区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8件,同比下降92%;普洱中院院、庭长审结案件377件,人均结案41.9件……
数字是枯燥的,数字背后的改革内容却是丰富的。试点法院的改革凝结了云南法院推进改革的勇气和担当,也标志着司法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如今,司法改革工作已经在云南全面推进,在阵痛之后,必将迎来收获的喜悦。(茶莹 姜光鑫)
来源:人民法院报
责任编辑:李彩霞